在生命的最後,我們能否擁有選擇醫療方式的權利,並且作好該作的準備?《病人自主權利法》上路6年來,雖然簽署人數逐年增加,但這樣的討論是足夠的嗎?許多人並非拒絕,而是不知該如何開口;家屬與病患的想法時常不一致,談論死亡是一件不熟悉的事。透過採訪第一線推廣者與醫療現場的故事,揭示《病主法》落地的挑戰。
「我想簽啦,但我女兒不讓我簽,她說那不吉利。」
關於《病人自主權利法》(簡稱病主法)的社區宣導場合,70 多歲的阿嬤舉起手,小聲說出這句話,現場頓時安靜下來,真實地揭露了這部法律落地、推廣過程所面臨的困難之一——不是內容不清楚,而是有些話太難開口。
《病主法》上路6 年,簽署份數的統計數字逐年上升, 看似制度落地的進展。但走進宣導教育現場,仍可看見一雙雙遲疑的眼神,以及一場場誰也不願先開口的沉默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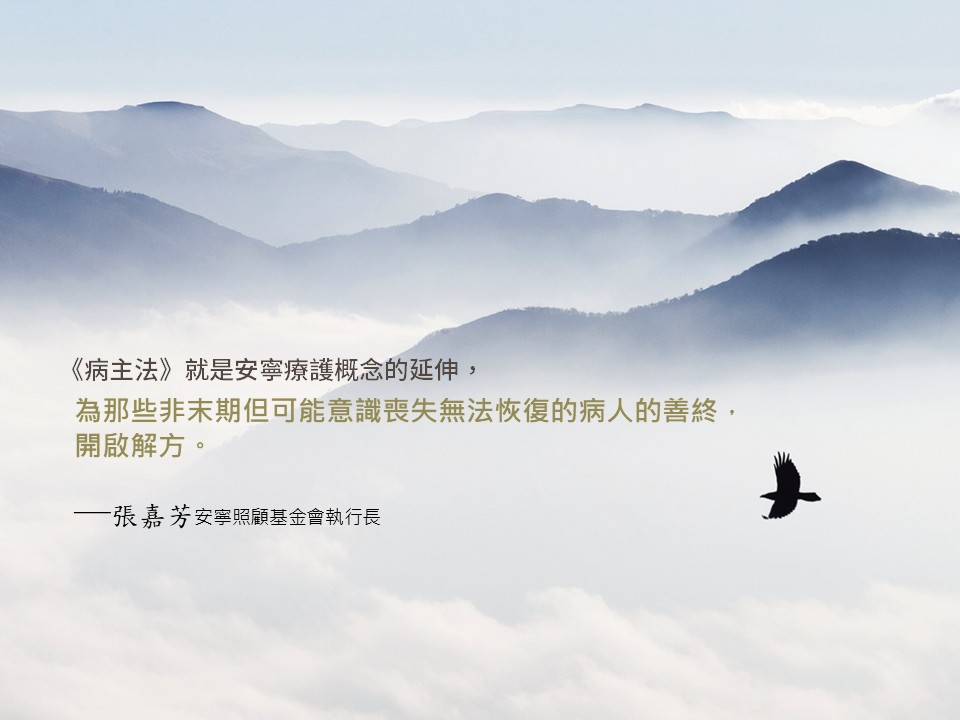
不是反對而是不知道怎麼開口
安寧照顧基金會於25年前推動《安寧緩和醫療條例》上路,當時的目標,是在保障末期病人在臨終時,得以合法選擇免受急救之苦。執行長張嘉芳表示,「自2010 年起,基金會首開先例推動『預立醫療自主計畫』,因為我們當時看到,仍有許多病人雖非末期,卻已陷入無法恢復的意識喪失狀態。」若能在病人意識還清楚時,有機會表達自己想要或不想要接受的醫療處置,將能確保在失去意識或表達能力後,仍依照本人意願進行想要的照顧。而這,就是《病主法》應運而生的源起。
「《病主法》是安寧療護推動的延伸,為非末期且可能意識喪失的病人,開啟解方。」張嘉芳說,安寧不是消極地等待死亡,而是幫助一個人將自己對生命的價值觀貫徹到最後一刻。而《病主法》則是透過「預立醫療照護諮商」(Advance CarePlanning , ACP),以及簽署「預立醫療決定」(Advance Directive,AD),讓這個意願可以提早被討論;選擇可以被表達。
一個人的生命走向關機,需要的不僅是醫療照顧,更需要靈性的安頓、關係的修復。東海大學社工系助理教授葉依琳說,安寧緩和醫療提供溫柔的照顧,而《病主法》給出選擇與方向。「預立醫療照護諮商」不是在教一部法律,而是陪著人們練習說一件很難說的事。
「我在做ACP的時候,可以很清楚看到,許多人是第一次坐下來跟家人談死亡。」葉依琳同時也是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人文創新書院前組長,她曾長期站在第一線擔任安寧病房社工。她說,許多人從來沒有想過,自己可以選、可以拒絕、可以留下交代。
作為《病主法》的立法推動者,為愛前行基金會創辦人楊玉欣說,最大的問題還是「很多人根本不知道《病主法》的存在」,在她倡議、推廣《病主法》的過程中,經常遇到民眾說「我有簽了啦!」但其中有人誤以為預立醫療決定就是不施行心肺復甦術同意書(DNR),有的人只是模糊跟家人說過「到時候不要太辛苦」,就以為具備法律效力,這些都是常見的資訊落差。
我們的社會還沒習慣談死亡
張嘉芳指出,安寧照顧基金會推動《病主法》,最常遇到的不是反對,而是理解過於片面或是過於簡化。「社會的問題不是拒談死亡,而是從來沒練習好好談死亡,也沒有養成討論的習慣。」她坦言,許多人沒有先做Pre-ACP,也沒與家人討論,就直接預約ACP門診。許多觀念、想法、價值觀都不可能好好討論。雖然社會風氣漸開,接觸死亡議題的機會不少,但多數人不知如何開口,也沒有花時間與家人討論,以為簽了AD就等於善終,簽完也不再討論,造成幾年過去可能連當初自己簽了什麼都印象模糊。這樣一來,真正需要啟動時,反而容易引發醫病之間的緊張。
葉依琳也分享自己在北市聯醫的觀察,她說,這個沉默不是偶然,而是集體的壓抑。「大家其實都知道彼此的意思,但都不願意先開口。」她說,有些末期病人其實很清楚自己的狀況,也不希望經歷無效治療。但他們不敢開口,怕一談死、家屬會哭;而家屬覺得主動開口像是一種詛咒,自然也不敢提。於是,最常見的就是彼此「裝沒事」,一個不敢說、一個不敢問。
直到病危那一刻,醫療體系只能照慣性全力急救——這便是葉依琳最不忍看到的場景,病人病危時,醫生在病床前問家屬:「現在要插管了,你們要不要急救?」在這樣的情況下,家屬根本無法理性思考,只能用情緒做決定,「救!」,然後在猶豫與淚水中讓醫療繼續下去。其實,推廣《病主法》的關鍵從來不是醫療本身,也不在表格的填寫,而是討論的意願。

每個人的善終都該由自己定義
「其實我爸有談過善終,他說他不要救。」葉依琳說,有時聽到病人家屬這樣講,她一定會再問一句:「你知道他說的善終是什麼嗎?」往往會聽到讓人預想之外的說法。
這個時代的「善終」,似乎有了一種被大眾定義的僵化版本。很多長輩只說一句「我什麼都不要插」,卻說不清楚不插的是尿管?鼻胃管?還是氣管內管?葉依琳建議民眾應練習完整溝通「如果沒有機會,我不要插管」;或是「哪一個處置能讓我比較舒服?」臨床上,不乏拒插尿道,反而造成漲尿解不出而更痛苦的案例。
「有些人覺得不插管才是尊嚴,但對於想選擇救到底的人,也應給予尊重。因為這都反應自己的人生信念。」張嘉芳說,這正是《病主法》的精神,重點在於思考清楚,願意與家人討論,自主意願都應該被尊重。「善終」不該有標準版本,而是回應每個人不同的人生背景、價值觀與信仰,那場對話真正要談的,不是「怎麼死」,而是「怎麼活到最後一刻才是我想要的樣子」。
楊玉欣後來乾脆不再用制度語言去介紹《病主法》,而是這樣說:「這是一封你寫給未來家人的信, 告訴他們你希望他們怎麼陪你走最後一段路。」她說,如果語言太冰冷、太陌生,人們會本能排斥。但簽署本身不是目的,有品質的諮商才是。《病主法》所影響的,不只是撤除儀器或放棄搶救的那一刻。它是一場生命與關係的對話—— 你的告別式想怎麼辦?你希望孩子在哪裡懷念你?你想留下什麼給這個世界?那些說出來的,不只是選擇,更是價值。

推廣的現場不該單靠熱情支撐
但要讓這場對話發生,不能靠制度口號,更不能靠醫療體系「順便推動」。
「其實,如果有經過ACP程序,屆時不論病人是否有表達能力,醫師只要依照AD執行,就能獲得100%的法律保障,這是對醫生的保護、也是建立醫病關係的基礎。」楊玉欣更指出,依照目前規範,ACP只能由醫療院所來執行,「若能讓更多民間團體也加入協助,不僅可提高服務的總量,讓民眾盡早完成ACP,也能適時減少醫療機構的負荷。」
張嘉芳也認同ACP需要的是時間、空間與情感支持,然而,目前的制度設計讓第一線的醫療體系承擔龐大的臨床工作,即便大醫院也無法長期排出人力,何況是偏鄉醫療機構。
「我們讓ACP變成制度流程,但並沒有變成醫療文化,一線醫療人員如果沒有被培訓、理解核心價值,不會真心想做的。」葉依琳分享過去北市聯醫經驗,她說,當時是從院長拍板力推,並從「生命識能」的角度出發,未來應加強讓社區的居服員、照服員成為第一線的接觸點,在照顧長者時引導思考,接著才慢慢媒合到醫院做正式的諮商與簽署。
造成制度無法落地的原因還關係著資源分配。張嘉芳說,進行一場ACP的費用目前大約是3,500元,看似合理, 但醫療端與民眾端認知期待還有落差。她坦言,現行制度是靠燃燒熱情的「好人們」所撐起,無法長久支援。應該有一套合理的制度,讓有意願的人能夠持續做,同時也必須有誘因與責任制度,讓醫療單位知道這是基本責任,而非附加選項。

弱勢不能被選擇排除
要讓ACP的品質提升,只能由民間團體補起制度不足下的缺縫。楊玉欣表示,第一步就是確保疾病纏身、資訊落差,以及身障造成溝通與行動困難的弱勢族群,不要丟失了自己的權利。她印象最深刻的一位罕病病友,就是秀秀。
她是一位小腦萎縮症患者,心智清楚、但完全無法說話。發病後,她看遍許多重症臥床的病友,沒有生活品質地度過多年漫長的生命時光。她在楊玉欣的邀請下,參與《病主法》的倡議,盡力地用手比劃表達立場。秀秀的母親對於女兒希望簽署預立醫療決定,並捐出自己的腦用於醫學研究的想法,她完全尊重和支持。秀秀的母親事後回想,雖然心中萬般不捨,但想到這都是女兒的心願,白髮人送黑髮人的傷心也至少能夠安放。
「《病主法》的核心不只是末期病人,我們長期推動『弱勢服務方案』,就是為了協助家中有身障或重症病人的家庭。」楊玉欣說,不是每個患者都跟秀秀一樣有機會充分認識《病主法》,常常是照顧者先倒,因為壓力太大。
集結全國28 家醫院推動而成的「弱勢綠色通道」就是因此而生,協助偏鄉、罕病、障礙者,或是高風險家庭到醫院進行ACP。起初障礙重重,醫療院所沒錢、沒人,便由病人自主研究中心、為愛前行基金會自行募款,訓練人力,才能成功串起這條通道。
「這不是制度該有的樣子,但如果連我們都不做,誰來保障他們呢?」楊玉欣目前也推動「一加一、一加二」方案,讓病人可以帶著1 至2 位家屬一起接受諮商,幫助他們建立醫療決策共識,把選擇談清楚,不要讓最愛的人在無知與恐懼中走完最後一程,甚至讓家屬在身後受苦。

未竟之路陪你把話說完
對第一線推廣者來說,《病主法》這6 年來最難的,不是制度太難懂,而是讓人願意開口。再多的簽署數字,都比不上那一刻—— 一個人真的坐下來,對所愛的人說:「如果那一天到了,我想要怎麼走。」
這樣的談話,不會自己發生。它需要有人陪、有人解釋、有人願意慢慢等一個家庭把話說完整。但現在的制度裡,推廣者常常只能用熱情補位,用時間堆疊信任,等待制度更齊備的一日。
我們還沒走到理想的終點,但這條路不能停下來。推廣《病主法》的意義,不只是希望人們學會選擇,更是讓他們知道,「當你想說的時候,會有人在現場傾聽,把你的話當作最重要的事」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