筆者回顧過去30年間走訪丹麥、荷蘭、挪威、芬蘭各國的經歷,深入觀察這些國家在安寧照護領域的發展與成就,並汲取了寶貴的經驗。當他最終回到台灣,比較國際間的先進做法,對台灣的安寧照護現狀也產生了更深刻的理解。
我在1990年是全職新聞媒體人,開始注意安寧是因為有位學護理的姊姊,鼓勵我採訪新聞時,可以多注意國內外安寧的發展。
丹麥
深刻的聆聽與尊重
2005年因採訪工作來到丹麥,去了安寧專責醫院「Sankt Lukas Stiftelsen」,我印象最深的是,當我敲86歲護理長辦公室的門,她說「我在聽」。她要讓我知道,我在她面前被聽見、被看見。很多年後,我明白這對病人,甚至任何人都是那麼重要,感受到自尊與價值,可以紓解苦痛、煩惱與表達一切心裡的話。
她又提醒我,千萬不要在病人旁邊聊那些「有的沒有的」,因為他們都聽得到。不要讓照顧者的聊天成為動不了的病人的災難。
該醫院每間病房牆壁上有許多空間,隨時替換入住病人期待的裝飾。這部分荷蘭已經有數位投影可用於任何方便病人視覺的角度。
在丹麥學習居家服務時,遇到一位每天要換嗎啡貼布的長者。印象很深的是,長者因與每天笑容可掬的居護師聊天而不覺得孤單,2人關係不僅只有疾病與失能。居家服務有3種顏色藥盒,分別是家屬可開、居服員可開,和護理師可開的管制藥物,資源配置完善。照顧者得以更多時間專注在回應病人。羸弱的病人受到支持,甚至有力氣和我聊以前來台經商的事。
荷蘭
理解安樂死與加工死的辯證
1995年至2016年在荷蘭公視學習時,發現有個專門拍安寧病人生活的電視節目。有位病人拍攝長達19年!也就是瀕臨死亡這麼久才結束拍攝,因而變成特別節目。即使有進步的醫學判斷,但生命的事很難說。因在荷蘭住一段時間,我或許是最早拜訪荷蘭安樂死協會的台灣人之一。看著他們一排人如何進行電話諮詢,我好奇是誰將中文翻譯為「安樂死」? 更準確來說,其實是「加工死」。我認為有些病人其實有現代醫療可以緩解,之所以選擇加工死,和活著感到失去意義和自我肯定有關,而不像媒體說的只是身體很痛苦。
我的荷蘭朋友甚至訪談過7位失智者選擇走這條路,寫成書後,她決定絕對不走這路,因還有很多方式可以走向未來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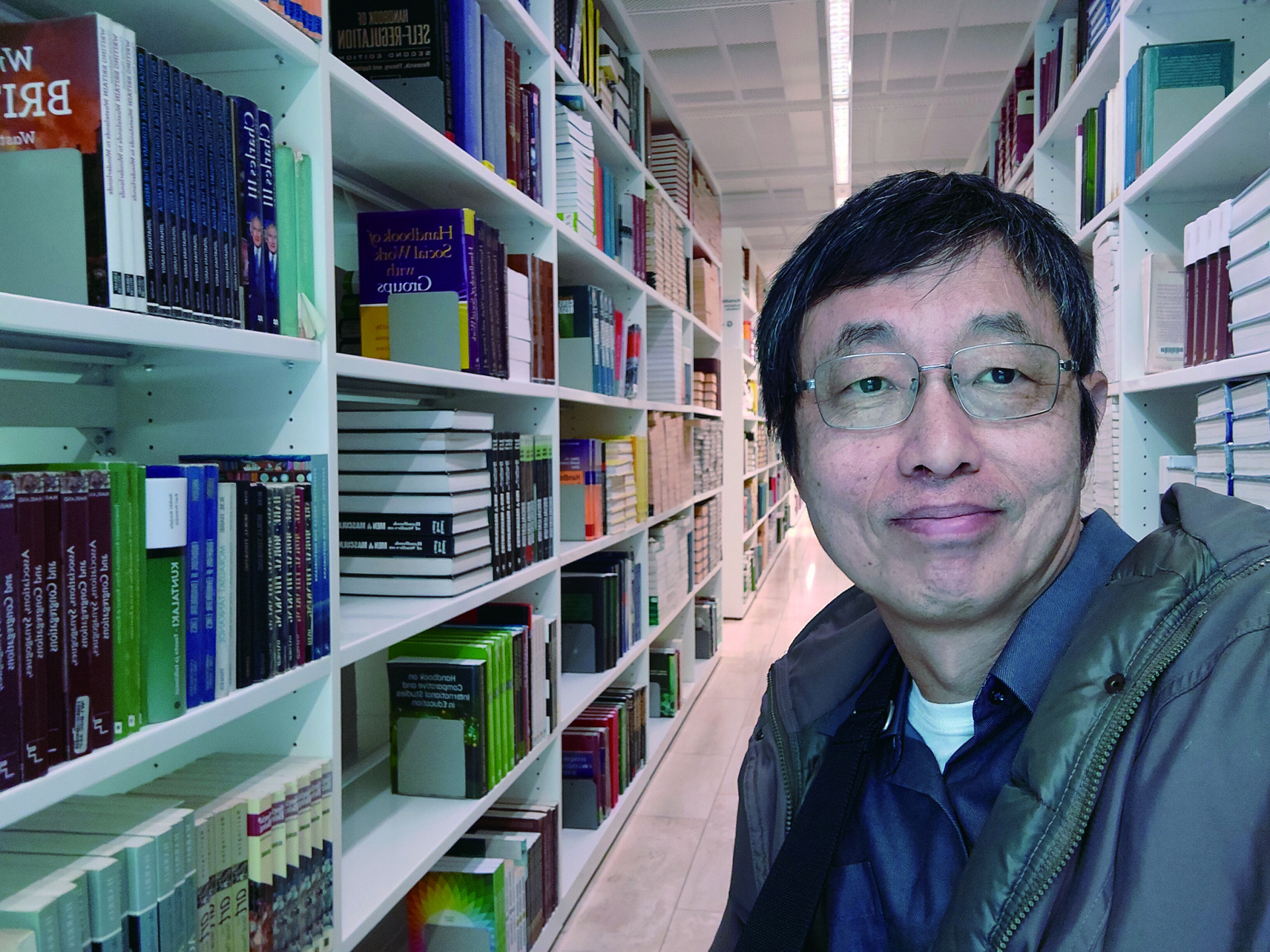
挪威
實現全方位的照護理念
2007年到挪威首都奧斯陸風評最好的安寧醫院「Lovisenberg Diakonale Sykehus」。有病人來這裡彈吉他交朋友,甚至與醫療人員一起出版CD,錄製好聽的歌曲。病人穩定可以回家時,醫院有安寧小組會聯繫當地家庭醫師與居服員接手,有問題隨時一起討論因應。如果有任何需要,就近的護理之家有安寧喘息與緊急處理保留床,不必回大醫院,減少病人與家屬折磨。也有新的社區健康中心,設有特別設施方便病人洗頭等舒適護理的空間,隨時可接手來自居家的末期病人。
挪威另有家醫院旁有個生命療癒花園,讓病人家屬可以散步,燃起對生命的盼望。學習後,再看到國內的相關設施就感覺氛圍差別很大,絕對不只是病房旁的水泥地弄幾盆花、推輪椅透透氣而已。
醫院同時考慮到安寧團隊的辛苦,有專門給團隊使用的舒壓水療池。2016年我遇見挪威衛福部長,他特別推薦一處健康中心,除了有安寧病房,還有間漂亮舒適的房間,是為實習護理師預備的休息與學習空間。理念是,善待實習生,他們才會覺得這是值得投入的工作,進而招募到有意願、有素質的後起之秀。
芬蘭
理解安寧照護的深層價值
2004年在芬蘭,遇見曾在恆春基督教醫院服務,幫助無數痲瘋病人與外籍配偶的馬護理師,她退休回到芬蘭,下背痛已經非常難受(在台灣照顧且搬運病人30年),只是禱告希望上帝接走她。我問她對荷蘭加工死的看法,她說生命是上帝給的,痛苦可以有很多方法減緩!芬蘭有專門研究如何照顧受苦者的看護理論(Nursing Theory),我有幸在芬蘭向有充分實務經驗的教授們學習。他們用愛與慈悲關懷之心,引導且支持病人找到信、望、愛。讓我們看到,安寧不表示一切活在絕望中。如同前面許多故事,若是照顧者對生命有謙卑智慧的省思,就可以幫助病人與家屬更多。
韋至信醫師曾說,能活下去就是因為找到、感受到意義。由此看來,意義,未必是新聞報導的,如推到海邊看海或吃什麼食物的圓夢,仍能幫助別人也是一種生命意義,而且是很大,甚至永恆的意義。
台灣
尊重末期病人的生活樣態
2023年回國後,對安寧照顧更為留意。曾隨安寧居家醫師家訪一位末期病人,他很想以口進食,但兒子擔心爸爸吞嚥困難容易嗆咳。我隨即聯繫語言治療師,幫助解決疑惑。這事讓我感覺到,即使這麼艱難無助的居家個案,只要我們有心,就可能有不一樣的機會。這是很大的支持與盼望!真的需要集思廣益、謙卑以對,才能找出對末期病人最適當的照護。
又隔不久,我兼職居服員,有次接手一位剛出院的末期老人。前班居服員交班這一安寧個案,只要定時管灌牛奶、換尿布、擦澡即可。我很懷疑90小時養成的居服員,對安寧的定義是否有清楚的理解。當天接手後,我盡量與老人家互動,用觸覺、友善言語,再引導長者坐起,支持下床如廁,血氧從83升高到92。同時,我再用LINE向多位營養師與物理治療師討論現場狀況來調整照顧。幫長者洗完澡後,他在床上表示想喝水,我一時沒聽懂,他用力改說「茶啦」!看著血氧越來越高,突然發現,原來居服員偶爾沒聽懂、讓長者生氣,也可增加活力。
後來病人越來越清醒,不願在床上大小便。想下床如廁,女兒怕他摔倒,我評估建議協助下床。在廁所,長者示意要衛生紙,女兒回說「你擦不乾淨啦,我們等一下幫你」,我則建議讓長者自己擦,這是尊嚴自主,有助體力恢復,真不乾淨再幫忙。眼看他精神更好,結束了當天6小時的喘息服務。10天後,我特地去探視他,老先生拿著助行器快樂的從屋裡出來和我打招呼,因此發現,如何協助病人保有他期待的生活樣態,也是安寧療護的精神。
展望未來,醫療技術將更發達, 脆弱而未離世的人很多,到底什麼樣子需要安寧照護?可能定義更寬,人更多,未必僅指癌症,也可能只是衰弱,還有失智安寧(丹麥等國非常先進)等各式各樣的分類,都有待學習發展。願我們一起努力,讓安寧隨著時代轉變,更科學、更人性。如丹麥護理倫理所說,「當我與你在一起,我就無形中占有你生命的一部分,因此,接下來你的感覺好壞,我有一分責任」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