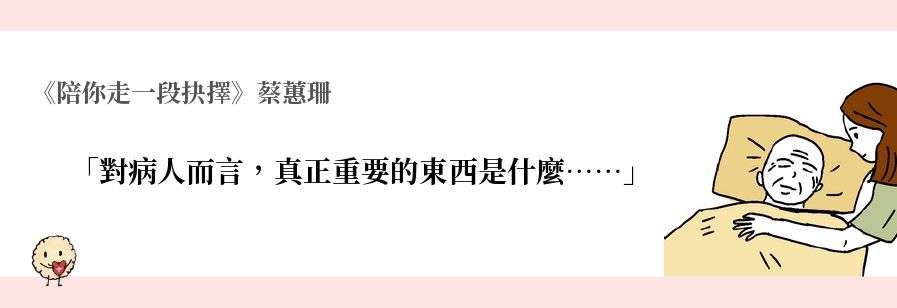
身為安寧緩和醫師,我偶爾會穿梭在加護病房,協助原團隊醫師做末期判定,或經由家庭會議協助家屬做醫療決策。依據法律規定,唯有兩位專科醫師診斷末期,病人才能如願以償取得善終的門票─撤除維生醫療,走向臨終。
第一次見到高伯伯的女兒,是關於撤除呼吸器的家庭會議,她淚流滿面地問我,她是不是做錯了,爸爸留下遺書想要告別,卻被她硬生生地拉回來。我無法回答她是或不是,非黑即白的二分法太過殘忍,我只能回應她,如果今天是我的父親,我可能也會這麼做。
心疼親人受苦的煎熬
高伯伯在前幾日燒炭自殺,女兒發現後急忙將父親送至急診, 經過一連串插管急救,命是懸住了,人卻是昏迷的,滯留在加護病房。女兒們後來發現爸爸留下的遺書,寫著:「身體已是垂垂老矣,怎堪病魔反覆折騰?切勿再積極搶救,徒浪費醫療資源。」
而今,這字字句句呈現在我眼前,女兒懇求為父親撤除呼吸器,完成他的心願。「有醫護人員問我,如果不想救,當初為什麼要送急診?我說不出話來。我當下真的慌了,想都沒想就送來了。」女兒不斷地自責。這一句話點醒了家屬,卻把他們推向更深的內疚。
自殺的腦傷病人是不是末期?這是個灰色地帶,原團隊醫師不認定是末期,卻也明白後續病人會臥床且每況愈下。家屬尋求撤管已不可行,安寧緩和的介入主要在情緒支持。
幾日之後,病人成功脫離呼吸器轉入呼吸照護病房,薦椎附近卻出現褥瘡,於是接受開刀清創,之後必須持續換藥。女兒的情緒似乎慢慢撫平,面對既成的事實,決定好好振作,尋找能照顧父親的養護中心。
再次見到他們是三個月後,高伯伯因褥瘡感染而住院,女兒堅持一定要會診安寧團隊,拒絕原醫療團隊提議的再次清創或任何侵入性治療。「我爸爸正是因為害怕現在這種狀況─臥床、長著褥瘡、插著鼻胃管,所以才選擇自殺,怎麼現在又一步步走到這模樣?」女兒在病房走道上問我。這一次,原照護醫師同意診斷末期,我們終能啟動安寧照護。
我們與家屬達成共識,停用抗生素,僅維持基本照護:換藥、翻身、清潔與症狀控制。在沒有任何醫療處置之下,高伯伯的病程再次趨緩下來,過了幾天出院返回養護中心。有時,我會覺得,人會不會活下來,或許自己的治癒能力才是關鍵,外在醫療並不如我們以為的重要。
因愛放手,讓您好走
高伯伯出院後轉由安寧居家療護接手,我們每兩個星期會到養護中心訪視高伯伯,他規律地使用退燒藥與嗎啡,發燒與喘緩解許多,唯一的問題是褥瘡愈來愈深,已可見骨,舊傷未癒,又長出新的褥瘡。每次換藥他都皺著眉,緊繃著身軀,大力呼吸,雖然無法言語, 可任誰都看得出來他不好受。在長照機構,臥床病人的生活大多是如此:無止境地換藥,無止境地翻身,無止境地灌食,無止境地等待, 可能是等待親人的到來,可能是等待結束的終點。
「蔡醫師,像他這樣如果一直灌食,是不是沒有終點?我們可以停止灌食嗎?可以不要再違反高伯伯的意願了嗎?」居家護理師沉重地問我。是啊,《病人自主權利法》已同意在病人不可逆的昏迷時,可以終止給予人工營養或流體餵養,像高伯伯已表明自主意願,家屬也毫無疑問地支持,我們醫療團隊在糾結什麼?
於是,我們向家屬提議終止人工營養,女兒們同意並且選擇再次入院。一旦停止灌食,就進入臨終的階段,這一次我們心裡明白,是最後一程了。預計入院的前幾天,高伯伯情況有了波動,偶爾會喘起來,體溫時高時低。入院當天,我們剛接待完高伯伯,安頓好床位,他轉眼間就離開了。
「爸爸可能等不及,先走一步了。」他女兒告訴我們。這是我轉換醫院後,陪伴最久的家庭。關於生命的課題,有太多需要去深思的事,如果我們只以二分法,將醫療區分成「救」與「不救」,對家人而言,是一個極度殘忍的宣判;對病人而言,真正重要的東西是什麼,我們會看不清。走在安寧的路上愈久,愈加感受到生命抉擇的困難。
作者介紹
蔡蕙珊
從住院醫師踏入安寧緩和醫療的那一刻起,我再也沒有轉身離開過。回首一看,已過了數十寒暑,這一路,我從對安寧照護的懵懂與困惑,到現在的透澈與堅定,是因為無數病人給我的生命習題歷練而來。
習題上的文字,有時深刻激盪思緒,有時輕柔擁抱靈魂。偶然想起之時總會明白,這都是我的一部分。
